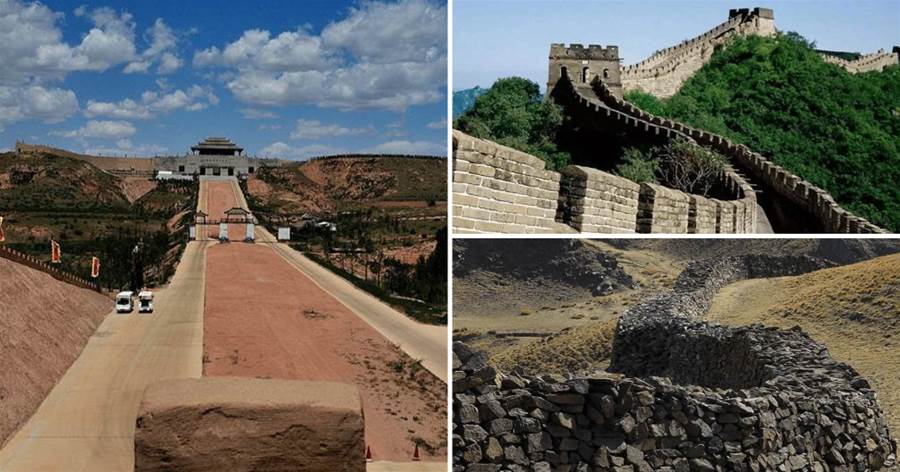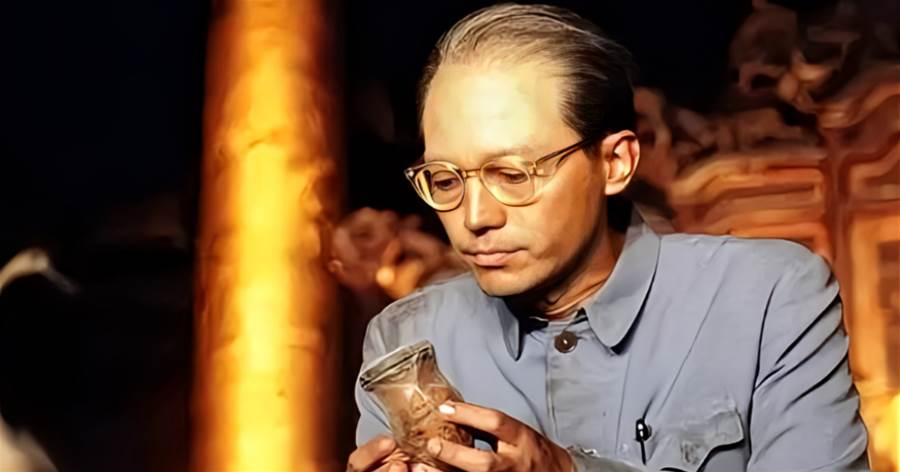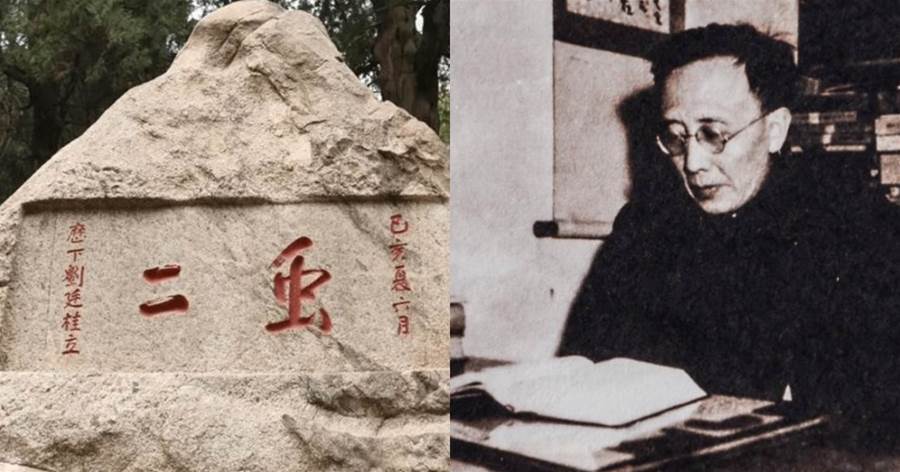12年廣東水底現大量女性骸骨,考古隊考察,揭開一段殘酷的黑歷史
2023/11/29
在2012年的廣東梅縣,一個名為綠窟潭的水下溶洞中,探險隊發現了大量女性遺骸。根據現場分析,這與傳說中的「浸豬籠」別無二致。將不守婦道的女性放在籠子里沉塘,以此維護家族名聲。
這些亡于禮教的女性,成為一個時代悲慘的記憶。想要了解這段黑暗的歷史,我們不得不從先秦時期開始分析,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殘酷的事情。
ADVERTISEMENT
先秦禮教
四大文明古國中,每個國家都是以農耕文明為主體。在這一期間,我國從母系社會轉入父系社會。男性以其體力的優勢巨大,決定了生產方向和話語權,繼而成為部落的領導者。之后的千百年來,我國一直以一種男耕女織生產組合延續和發展。
養蠶繅絲的嫘祖,發明車、船的黃帝,這個時候,無論男女在生產方面都有貢獻。甚至商朝以及周朝早期,女性仍然能夠參與政事,例如打敗雅利安白人入侵的婦好,就是華夏第一代女將軍。
可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生產力的提升,老百姓儲存的糧食越來越多,不用餓肚子的人們有足夠多的時間進行思考,發展文明。

ADVERTISEMENT
于是文明開始爆發,最終在春秋時期到達頂峰,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,也開始了對女性的約束。
即便在這個時候,部落成為國家,人民之間也有了貧富差異,但男女依然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。
文化發展
「關關雎鳩,在河之洲;所謂伊人,在水一方。」春秋時期成書的《詩經》中,有著大量歌頌青年男女愛情的詩句。除了《關雎》中的男追女外,更是有許多女追男的案例。
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嚴禁無授權轉載,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。
ADVERTISEMENT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